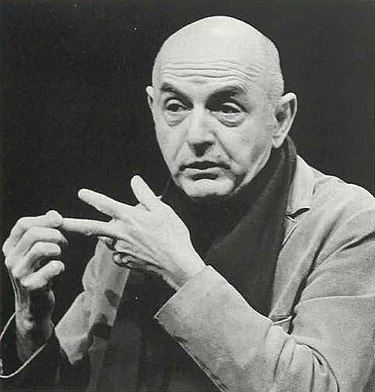老生常谈了这次介绍下无聊的德国的贝恩德和希拉·贝歇尔夫妇(Bernd & Hilla Becher),号称德国摄影艺术先锋也曾是与杜塞美院教师,他们实践的“类型学”摄影,以无表情拍摄(Deadpan)为技术特征,通过他们自己的创作,更通过他们的学生引起强大的杜塞尔多夫效应,从而引领了德国当代摄影的方法论、技术美学与风格潮流。

贝恩德(1931—2007),生于德国锡根,曾师从著名画家卡尔·吕兴学习绘画和素描。希拉(1934— ),生于德国波茨坦,曾给当地一位摄影师当学徒,这位摄影师存有以前无忧宫御用摄影师们的档案。两人1957年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广告公司认识的,于1961年宣布结婚并一道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他们导师是一位和善的图形学教授,两人由此开始了长达一生的摄影搭档之旅。

他们的第一个项目取名为“框架房屋”,这个项目持续了近20年,后来出了一本画册《框架房屋》(1977/2001)。
60年代,他们的主要拍摄项目是重工业。当时整个重工业建筑群都面临着关闭或拆毁的命运,夫妇俩赶在消失之前拍下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旧工业建筑。他们的第一本书《无名雕塑:工业建筑的类型》(Anonymous Sculptures: A Typology of Technical Construction)由七个章节组成:“石灰窑”、“冷却塔”、“鼓风炉”、“提升塔”、“水塔”、“储气罐”和“地窖”。1963年,他们举办了第一次展览。

◆贝歇尔夫妇对于工业建筑摄影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他们的图片从最初出于纯粹的记录走向概念的表现。
贝恩德的第一张工业建筑照片是在1957年拍的,当时他在一处正在被拆除的工业设施中画素描。素描的速度显然及不上拆除的速度,为了完成这些素描以便为后来需要创作的美术作品提供参照素材,他拍摄下了这处建筑。消失中的工业建筑令贝恩德起了强烈的用影像存留下它们的念头。
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后,他们开始拍摄工业建筑的照片并将之分类(德国人的特性就是删除分类,他们的口头禅就是ALLES IN ORDNUNG)。贝恩德曾被问及拍摄出于哪种动机——是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还是撰写工业历史的一部分,或者作为一项艺术事业?贝恩德说他最先并不赞同像雕塑家汀格瓦立(Tinguely我很喜欢比贝歇有热情的多)那样以“艺术—工艺”的形式来诠释工业,但后来他改观了,因为汀格瓦立用各种工业废弃物组成的雕塑作品让人们有机会看到过往旧物的美好之处。这些旧物如同纪念碑,并且有着丰富的细节。贝恩德认为对于这些旧物,比如某座铸造厂、某处煤矿,从其自身进行发掘会有趣得多。
于是,他们在冬季的月份里,在灰暗的天空下,用极为保守、清晰得没有任何瑕疵的画面如实记录下这些工业建筑,不注入一丝人为的情感,建筑物冷冰冰的,没有任何表情、刻板地显露出基本的物理特征。这种无表情拍摄一直是夫妇俩唯一采用的技术手法,这确实符合他们留存文献资料的初衷,也特别体现精准的德式风格。这些照片是非常合格的文献。
但给这些照片带来概念意味的是他们对照片的编排方式。在最初的展览中他们只是将照片镶在方框中,排成两排挂在书架前面,一排在另一排的下面,这种整齐的排列方式确立了一种分类编排,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寻找照片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上。进一步明确的类型化的想法是他们从收集到的关于某一主题的庞大资料中产生的。他们于是采取19世纪应用于植物学和动物学的百科全书的方式,对正在拍摄的建筑物进行明确的分类,从而让它们分属不同的种类、亚种类。这种分类法是一种古老的方法。稍后,这种方法又在概念艺术中得到合理的充分应用。

在这里有一点可以得到启发,在技术层面以见证式手法如实记录相机前存在过的物或事,是指记录式手法,是说明性的;而影像捕捉的过程与结果寻求对图像内容代表的意义作如实呈现是一种特定的精神追求,这是意义解读性的。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把两者混淆了,都用纪实来称谓,其实完全是两码事。当手法服务于这一特定精神追求时记录式说明与纪实性解读重合,当记录式手法服务于概念主旨时,它只是概念的必要手段。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代艺术中概念与纪实的互涉,其实发生在不同的两个层面,“概念式”摄影是指观念性解读追求在技术上借用了纪录式手法来塑造记录感的幻觉。
然后再看夫妇俩对他们作品中一直阐释的概念的表述:“它们(工业建筑物)在被建造的时候很少考虑到美学构造,主要是考虑它们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当它们的功能丧失或者人类不再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注定要被拆除。”“人们通常会认为如果没有早期(比如哥特时代)的一些古老建筑,欧洲就是一个贫穷的欧洲。所以,由于人们对古代建筑的重视,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很多哥特式建筑、罗马时代的建筑。然而,对于工业时代的建筑,却不尽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照片会给人们留下工业时代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将随着建筑物的拆除而消失。”
当时的德国并未完全接纳贝歇尔夫妇冷冰冰的记录图片式的艺术。不过,来自纽约的波普艺术还是在相对较早的时候在德国登陆了,这就为概念艺术以及极简主义作了铺垫。接着这对夫妇的作品陆续在一系列重要的展出中露面。但对夫妇俩来说最重要的一场展览是1975年他们与罗伯特·亚当斯、斯蒂芬·肖尔等摄影师的作品共同在美国“新地形学”展览中的展出,此次展览意义重大,影响了整整一代的摄影师。他们展出了分类组图,初看上去挺简单,但事实上它们包含三方面基本差别:相似物体的相似形象,不同物体的相似形象以及同一物体的不同形象。有时贝歇尔夫妇甚至将这些表现方式融合在一起使用。图片与图片的组合方式形成了概念意义,这一点也恰是后现代主义摄影的一个特征——影像的解读意义不光存在于影像之内,也可能存在于影像诞生之前、影像组合之间以及影像之后的文化背景。
到了80年代,贝歇尔夫妇的类型学作品成为博物馆的主要展品之一。1990年,贝歇尔夫妇作为德国艺术的代表参加了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并获得了雕塑金狮奖。

◆当代摄影中的肖像与景观的无表情技术美学、类型学方法与概念艺术的结合就肇始于贝歇尔夫妇。贝歇尔夫妇于1976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创建了摄影系,这是目前国际上最知名的摄影系之一,它培养了目前国际摄影界最为著名的托马斯·鲁夫、托马斯·施特鲁斯和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等人。他们继承了贝歇尔夫妇极度冷静、作为“旁观者”的无表情技术美学,同时也继承了他俩以及更早的奥古斯特·桑德尔(august sander比他俩有味道的多了)的类型学摄影方法论。贝歇尔夫妇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教学才是他们的最大影响力所在,他们的学生构成的“贝歇尔学派”左右了当代摄影的潮流走向,形成了强大的杜塞尔多夫效应。当代摄影有两条走向,一条是这种以无表情技术美学与类型学为核心的德式“新纪实”风格;另一条便是以媒体化、表演化为主流的美式“新纪实”风格。其实所谓“新纪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纪实,首先是一种手法带来的风格,其本质往往是行为或概念的表现。
杜塞尔多夫效应下的“贝歇尔学派”又对夫妇俩的摄影理念作了进一步发展:
1. 强化了作品强烈的现场存在感,这一点成为“贝歇尔学派”重要的特征。贝歇尔夫妇的作品构图严谨,制作精心,单幅照片呈网格状被排布在一起,让人情不自禁细细对比,作品的意义在于恢宏的排列带来的整体性与描述性,而非单幅的影像。这种强大的现场存在感在学生们手中被进一步强化,其代表人物比如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从80年代开始,古尔斯基开始制作大幅照片。整个90年代,他不停地把摄影推向更大的尺寸。如今,他的一幅作品经常是2米高5米宽。他使用大画幅相机来达到最高的图片清晰度,然后再用电脑合成。他的照片无比清晰,你无法找到一个比他的角度更加全面的角度来看这个场景。他一直从远处拍他的作品,使得我们观者不会融会到这个情景中去,而是像他一样,纵观全局。看他的作品,我们感觉自己好像上帝一样从远处观看着由不同微小的部分组成的整体。
2. 保留了旁观者的气场,同时偷换了旁观者的不介入立场。从单幅作品看,贝歇尔夫妇还是属于影像的捕捉者,他们尊重旁观者的不介入立场,他们的涉入在于对影像组合的排列上。而他们的学生们则不同,他们运用电脑技术对单幅图像进行概念式加工,比如大幅图像是由无数局部图像拼贴而成,甚至像古尔斯基移除了莱茵河边的整座工厂,而托马斯·鲁夫在他拍摄的建筑外观上用数码技术“关闭”几扇打开的窗户。在学生们眼中,更注重的是旁观者的那种强大的“上帝之眼”的范儿,而不是真正的旁观者的客观精神。正因为此,贝歇尔夫妇的这些学生成为当代摄影的图像制造者中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与另一种影像捕捉者的趋势形成不同的路线。

◆摄影与艺术弥合距离也离不开贝歇尔夫妇和他们的学生们的贡献。使摄影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应归功于贝歇尔夫妇。他们编排呈现照片的方式使得最后得到的作品,充满系列性、表现性、抽象性,突显了比较分类法的魅力,艺术评论家们极为欣赏,它们作为当代先锋艺术的代表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展出,在市场上也很受欢迎。而贝歇尔夫妇的学生们如托马斯·斯特鲁斯、托马斯·鲁夫和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更是近年来摄影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在市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通过市场的认可进一步承认了摄影作为艺术的地位。
贝歇夫妇在2004年获得了由哈苏基金颁发的年度大奖(Hasselblad Award)。在哈苏基金颁奖的评语里如此写到:“贝恩德·贝歇尔夫妇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人为强行拉高的影响)。在过去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致力于拍摄和记录工业时代的遗迹和痕迹。他们自成系统的摄影作品是实用建筑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从他们的作品的形式来说,他们既是摄影家也是观念艺术家。作为‘贝歇尔学派(Becher School)’的创始人,夫妻二人通过特有的方式影响了一代纪实摄影师和艺术家。”